从“书”到“剧”的变与不变——从改编谈《长安的荔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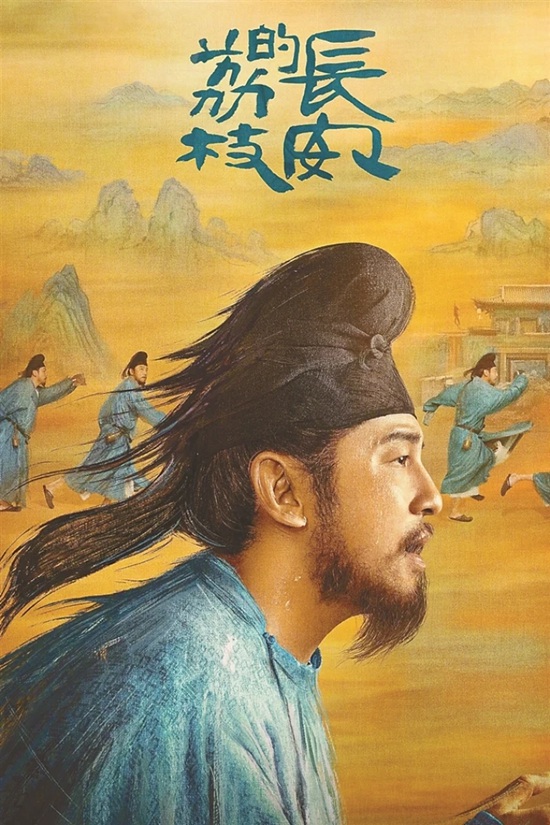
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海报
近日,根据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的剧集《长安的荔枝》在CCTV-8和腾讯视频热播。司农寺上林署小吏李善德跨越五千里把“岭南的荔枝”变成“长安的荔枝”的辛酸故事,摹画出唐朝天宝年间朝堂权谋的波诡云谲,刻画出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浮沉与坚守。从书到剧,变的是7万字到35集的戏剧容量,不变的是在历史讲述中不断寄寓现实思考的时代精神;变的是从单个人、一件事、一种个人与时代合一的结局,到双男主、多件事、主角任务与朝堂权谋映照,不变的是“显微镜下的大唐”彰显出的庙堂江湖气象共生的美,以及作者始终思索普通人生命体验、意义、价值的历史观。
在小说《长安的荔枝》的结尾,“安史之乱”终结了歌舞升平的盛唐岁月,被发配岭南的李善德已培育出无处可贡的贡品“丹荔”。面对现实世界和个体意义的坍塌,他一口气吞下30多枚硕大甘甜的荔枝,病倒在床上。这个开元年间明算科出身的“理工男”木讷呆憨,从遭人陷害以命博取一线生机的“荔枝使”,成为历史滚滚车轮下无语无望的“多余人”。刚刚平复不久的身心创痛再次排山倒海而来,苦尽却没有甘来的李善德像推着巨石的西西弗斯,重复着黑色而沉重的苦难宿命。在这场关乎皇权和人性的博弈中,无冷链的荔枝速递作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开启了李善德被权力体系暴力蹂躏的个人史。李善德的命运脉络,把故事焦点移动到“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另一面,为“无人知是荔枝来”提供了生动丰满的一种历史可能。《长安的荔枝》再次证明,把历史上普通人的命运放到显微镜下观察的结果,是历史韵脚的反复出场,是现实预言的不断兑现。这种由历史和现实互为镜像形成的生命体验的重合,既是马伯庸不断以“寻找历史可能性”为由笔耕不辍的引力,也形成了主角与读者、观众在异时空中共情共鸣的故事内核。
从小说到剧集,《长安的荔枝》延续了马伯庸历史小说的改编风格。在马伯庸的文学故事中,历史往往不是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而是小人物在特定历史时代中的生存博弈。“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的荔枝特性,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唐代成为权力对人进行压榨的符号。为了博贵妃生辰一笑,朝堂官府对强征民夫、累毙驿马、掀翻果园都大开绿灯。从荔枝品种到储存方式,从转运载具到运输路线,从气候水文到驿站调度,李善德虽极尽算法,却仍然无法算计人性险恶。无论是被鱼朝恩窃取札子,还是遭杨国忠强占运送荔枝方案,技术理性在权力游戏面前彻底失语。当请了一天假去“贷款”买房的李善德被上司和同僚算计落入“夺命荔枝局”时,我们仿佛看到了被困长安十二时辰的张小敬、身陷蜀汉谍海风云的荀诩,他们寂寂无闻又执着坚贞,他们忠于职守却又人微言轻,平凡的、普通的人物在历史长河特别是权力漩涡中的挣扎,成为书剧延伸的链接基因。
双线推进既是“马氏故事”的审美偏好,也是《长安的荔枝》充实剧情、加强戏剧冲突的不二选择。从人物形象的角度,小说中塑造的孤胆英雄李善德,在电视剧中则变为李善德和郑平安这对“郎舅cp”。新增的原创人设郑平安作为李善德的小舅子,是游走于三教九流的“陪酒侍郎”,一方面补充了李善德生活单调、老实本分的单一化形象;另一方面,二人在性格、经历、语言等方面形成的戏剧碰撞,让剧情的张力得到了更充分的释放。就叙事而言,该剧把“驿送荔枝”的单线任务拓展为“李善德运荔枝”与“郑平安查罪证”双线并行,李善德运送荔枝是奉右相杨国忠之命,郑平安同行岭南则为协助左相搜集杨国忠的贪腐证据。务实悲催的敕封“荔枝使”和圆滑世故的长安“飒骑马”二人一庄一谐,亲属身份、政治立场与人物气质相生相克,权谋斗争中不乏搞笑段子,在嬉笑怒骂之间勾勒出唐朝权力体制的“金字塔”,渲染出荔枝事件背后的历史景深。
值得一提的是,在剧版《长安的荔枝》中,轻喜剧带来的不仅仅是幽默的台词,更体现了喜剧对于思想和价值的包容。如果只有李善德苦苦挣扎的“技术型突围”而没有郑平安笑料百出的“社会化博弈”,历史剧难免表现出知识性叙事的迟滞和刻板说教的价值表达。在喜剧外壳之下,六部官吏推卸责任的“打太极”、岭南刺史何有光和掌书记赵辛民的“红白脸”、沿途各级官府懒政怠工的“踢皮球”等情节在笑过之后令人长叹。而郑平安原本出身名门望族,却在朝堂权斗和家族纷争中被逐出宗族,沦为权贵玩物。因此,剧版《长安的荔枝》中的双线之“双”,还包含一层悲喜交叠的黑色幽默韵味。
与《长安十二时辰》中长安城的明暗双线和《风起洛阳》中市井朝堂的双线不同,《长安的荔枝》在双线叙事中大大拓展了地理景观,把岭南民间与长安朝廷这两个距离五千里的地理方位并置,构建起一实一虚两个人文空间。在岭南的民间线中,通过李善德与峒人合作中呈现的歌声缭绕的荔枝园、烟火气十足的市集、酒窖祭拜后畅快的豪饮,以及与苏谅等盘踞岭南商业和政治版图势力的交集,生成了更有层次、更加丰富的民俗画卷。在这里,双线叙事上升为人生愿景与现实桎梏的互文,一边是李善德与以阿僮为代表的峒人不断破解荔枝保鲜难题,展现民间的生存智慧与朴素温情;另一边却是杨国忠等权贵为争权逐利,把荔枝转运异化为权力角力。这些情节在增加叙事容量的同时,也彰显了双线叙事带来的戏剧张力。
在剧之外,“李善德”的形象缘起于作者阅读古籍时看到安徽歙县一个名为周德文、负责物资采买调度的小吏。名字的确定则是在马伯庸看到一本敦煌写经卷子名录时,发现有一位名叫李善德的人,确来自唐朝,也确在司农寺上林署工作。为不配拥有姓名的“路人甲”命名,是马伯庸讲故事的习惯,现在看来,这些偶然又朴素的细节是历史显微镜能够聚焦的关键,应该也是《长安的荔枝》受到读者、观众喜爱的原因。
(作者系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中国文艺网
中国文艺网 文艺云APP
文艺云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