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宁:小说不是记忆,是现实的一些阴影
和周嘉宁约在一家有露台的咖啡店,隔着苏州河,我们能望见对面高楼耸立的中远两湾城——全上海最大的居民区之一。
“这里以前是上海的一个棚户区,叫潭子湾,差不多在2000年前后全部都拆掉了。”周嘉宁在2004年搬来这一片,当时周边还很荒芜,小区绿化也少,她眼看着那些小树苗一点一点地长大,长成今天绿意盎然的样子,“原来还有一个昌化路码头,据说今年又要重新通船了。”
这番讲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她新书《浪的景观》里的一些场景:码头、工地、高架、隧道、混凝土丛林、光秃秃的绿化带……它们正源于世纪初的上海,总给人一种灰扑扑的感觉。
那时周嘉宁刚上大学,经常骑着自行车四处乱逛,也在深夜望着工地里的庞然大物一脸迷茫:这个世界将通向哪里?会变成什么样?而回到复旦,校门内外也总在轰隆隆地建设,反复提醒着她到复旦第一天看到的一行字:THE FUTURE IS NOT SET(未来是不确定的)。
“但小说不是记忆。记忆包含了被篡改的现实,而小说是现实的投影。小说可能就是现实的一些阴影部分,或者说一些镜像的部分。”在《浪的景观》出版之际,周嘉宁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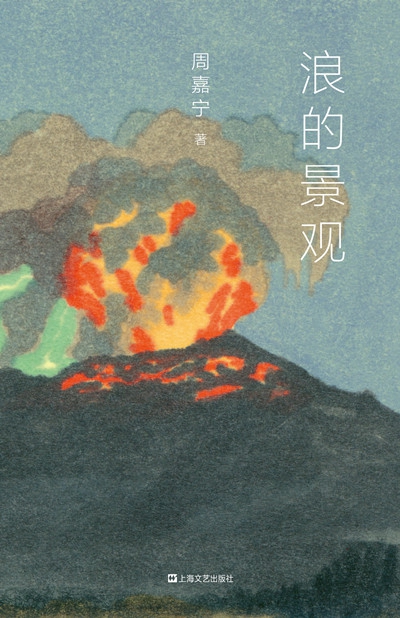
《浪的景观》刚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继2018年的《基本美》之后,周嘉宁推出了最新小说集《浪的景观》。这本书收录了三篇发生于千禧年前后的中篇小说——《再见日食》《浪的景观》《明日派对》,刚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世纪初的漫游介于即将逝去与正要开始的时代之间。身处其中的人们既为旧世界的颠覆感到不安,又暗暗期待新世界带来的希望。在周嘉宁的笔下,二十年前有人在失恋中写作,有人在地下商城赚到了第一桶金,有人在电台回溯二十世纪的摇滚历史,有人以特稿记录新世纪的一切……她在自己和他人的记忆里,写下时代之间的印迹。
三年来,周嘉宁放慢了写作速度,日常喜欢约上朋友在苏州河边散步,一走就是两三个小时。她熟悉苏州河四季流水的变化,熟悉两岸的植物与虫鸣,也在一些艰难或忧伤的时刻遇见了很美的月亮。每当这时,现实退得远远的,她不再说话,任思绪飘得更远。

周嘉宁
大伙凑在一起,想着“学校之外的事情”
作为年少成名的作家,周嘉宁的履历在互联网早已不是秘密:连着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考取复旦大学中文系、19岁就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2007年硕士毕业后去北京和张悦然一起创立文学MOOK《鲤》、2010年回到上海成为专职作家……但我还是很好奇,世纪之交时那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都在想些什么?
她从不写日记,但就在上个月,她找出了一张写于1999年12月31日的小纸条,上面只写了一个新年愿望:考上复旦。
和其他高中生一样,那时的周嘉宁以看书和学习为生活的主题。但有点不同的是,因为是青年报学生记者团的一员,她从高一就跟着一群高年级同学和大学生报选题、做采访、写城市观察。直到考上复旦,她也没有选择任何一个校内社团,而是继续待在记者团里。那是她学生时代最早的一个自己选择的“集体”,周围都是一群对文学或者流行文化感兴趣的人,大伙凑在一起,想着“学校之外的事情”。
那时她还喜欢听朴树的专辑《我去2000年》,仿佛生活中的一切都会和新世纪的到来联系在一起。朴树不算当时学校里最火的歌手,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听,但这一小部分人能因此成为很要好的朋友。考试结束后,她既放松又兴奋,和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一群人就在马路上旁若无人地唱起那张专辑里的歌。其中一首《妈妈,我…》,周嘉宁现在还背得出歌词:“在他们的世界/生活是这么旧/让我总不快乐/我活得不耐烦/可是又不想死/他们是这么硬/让我撞他/让我撞他/让我撞他/撞得头破血流吧/知道吗/我是金子/我要闪光的。”
“我觉得集体主义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那个东西不仅是你和学校的关系,也包括了你和社会的关系,包括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是怎么影响到你的。”她说,“我们这代人的成长时期已经改革开放了,能感到各种西方流行文化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涌入。但从本质上说,你从父母、老师那里感受到的氛围仍然是一种集体主义,所以当时你本能地想要逃离,想去追寻个人的意义。”但她感到有点微妙的是,等真的来到一个更为自由的个人主义时代,她又觉得集体主义在人生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想象中的“集体”,不再是现实中的东西
让周嘉宁对“集体”别有感觉的,还有一群伙伴。无论在《浪的景观》还是《明日派对》,抑或往前追溯《基本美》《密林中》,周嘉宁都写到了一种仅仅闪耀于世纪之交的关系:论坛朋友。对于今天还在写作的一批小说家而言,“论坛”仿佛是一条打开秘密通道的暗语。
高三暑假那年,周嘉宁家里买了电脑,她很快成为“暗地病孩子”“黑锅”“晶体”几个文学论坛的常客。这些论坛页面简陋,设计单一,却引来一群人在此流连忘返,肆意挥霍时光。论坛里有人写小说,有人写诗,也有画漫画的、做设计的、玩乐队的、拍照片的……大家似乎都很喜欢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发出来的文字大都奇奇怪怪,很短,很不“现实主义”。周嘉宁也在论坛上写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时她爱打“三角洲特种部队”,就在文字里模拟自己是游戏中人,在枪林弹雨中穿越各地。
当年的“刷论坛”很像现在的“刷微信”,她习惯性挂在上面,不时看看有没有新的帖子或留言。一旦有新的展览或演出,论坛里马上有人贴出消息。“那个时候小型展览和演出特别多,但很简陋,也不需要审核或许可,酒吧表演和live house都很繁荣。”每每去看展览或演出,很容易碰到论坛中人。大家在北京、上海、南京来回走动,看完了就一起吃饭,很快成为了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对我来说,最珍贵的应该就是认识了张悦然。”周嘉宁告诉我,她们在论坛认识时不到二十岁,虽然因为文学认识,但其实都还没开始真正的创作,都身处一个无意识的状态。“最初的相识和任何利益无关,甚至和文学本身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总觉得是论坛时期奠定了友谊的基础,有那个基础在,即使后来各自的人生境遇发生了很大变化,也能让这段友谊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她也隐约感到集体主义的含义在今天发生了一些复杂的变化,她难以描述清楚。她唯一清楚的是,她在小说里写到的“集体”已不可能在现实中存活,包括论坛,包括她在《了不起的夏天》里写到的以她个人经历为底色的北京申奥成功之夜——“迎面走来的陌生人互相致意,市民组成的锣鼓队来自四面八方。一些年轻人站在空的公交车顶上唱《国际歌》和《恋曲1990》”。
“这个夜晚再也没有被复制过,更不要说它变成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延续下去。它只能是一个想象中的‘集体’,不是我们现实中的东西,我觉得我写下这一段,是因为我非常清楚这一点。”
等到运气耗尽,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人生
上一本书《基本美》出版后,一个“90后”朋友好几次和周嘉宁说起:你们这代人运气真好。
她一开始本能地想要反驳,不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错过吗?她也会想起自己高中时听到了很多复旦传奇,比如中文系男生会找三轮车运来一架钢琴,然后去女生宿舍门口弹奏,但这样的浪漫永远仅存于她的听说和想象里。“高中时吸引我考进复旦的那些东西,似乎等我进去了就都没有了。”
但后来写起《明日派对》里的三个中篇,尤其写到《浪的景观》和《明日派对》时,她越来越意识到她这一代在世纪之交迎来青年生活的人确实拥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回想自己的青年时代,她现在也常用到一个词——“不可思议”,包括她的朋友每天放学回家要先听一两个小时的磁带,包括她自己会在高二会考前一个晚上跑去听郑钧的演唱会,以至于激动得难以入眠……这些在今天的她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
仔细想想,《浪的景观》里的两个男孩都没有很明确的商业目标,他们就是赶上了地下城的黄金浪潮,如有神助地赚到了第一桶金。《明日派对》里的两个女孩也不是专业出身,她们只是碰上了千禧年的电台光辉岁月,就做成了红极一时的节目。《明日派对》里写道:“我想所谓好运,就是专心致志的愿望终于得到来自宇宙的回应。 ”
但许愿的人太多,宇宙永远来不及一一作出回应。好在,“不成功”在那时候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写小说、玩乐队、排话剧、做当代艺术……谁有兴趣就可以加入,既没有管理,也没有标准,文学也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引进书和五花八门的奖项。一群并不明确自己想做什么的年轻人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尝试,或者说,他们可以在某种混乱和无序里非常盲目地生存下去,甚至可以在一些意外的情况下收获好运。
“问题在于,好运是不会持久的,它只在很短暂的一段时间里出现。等到运气耗尽,我们将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人生,这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年春天,周嘉宁和一些挺久不联系的朋友聊起来,大家因为疫情都有一种绝望的情绪,“好多人不约而同地说,之前二十年,我们已经把过去能感受到的好运都用完了。”
曾经的年轻人走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四下张望,焦虑而感伤。周嘉宁知道,她小说里的这些人,活到后来很可能也是遍体鳞伤的。
回望中的时光印迹,触发了一个个故事
每次出版新书,周嘉宁都会对“代表作”部分再做精简。在《浪的景观》里,她的作者介绍只提到了三本旧作:《基本美》《密林中》和《荒芜城》。
“我觉得以前写得很烂。”周嘉宁直言,她不会再去看之前的作品,甚至包括《密林中》,尽管《密林中》至少还有一些“幼稚但认真”的思考。“以前我太急于写出某一个时段的感受,但这些感受并没有经过思考,所以很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且从根本上讲,我以前也不懂得什么是小说。”
“那现在呢?你觉得什么是小说?”
“我怎么知道?”周嘉宁笑了,“我不知道多少写小说的人可以对此给出定义,难道不是应该要写一本书来讨论吗?”
“那你现在觉得小说跟故事是什么关系?”在我的感受里,《浪的景观》相比她之前的作品,有了更强的故事性。
“我觉得像《浪的景观》和《明日派对》,它们一开始触动我的起点都和故事有关,但都不是完整的故事。比如《浪的景观》的起点是外贸服装市场的一段往事,《明日派对》最初驱动我的是电台的黄金时代,我就想当时身处其中的人是一种怎样的状态?然后我的人物就产生了。”她回应道,确实是回望中的一些东西,触发了这一个个故事。
之前有读者评价这本《浪的景观》是用文学“做21世纪初的时间考古”。在她看来,考古依靠的不是记忆,依靠的是时光留下来的证据。有时它甚至不是你自己的证据,因为一些事发生的时候,大家都会留下证据。
“今天互联网上也还可以搜到各种线索,这些线索可以帮助你重新拼贴出那个时候的一些场景。”在写新书中的三篇小说时,她也通过各种方式去寻找当时其他人留下的记忆,“有时看多了别人的记忆,会有一种好像它们也变成了我自己的记忆的感觉。”
她偶尔也会看同龄人的创作,并从中看到他们共同拥有的时代印迹,以及那些印迹对他们这些人现在创作的影响。“这部分观察还蛮有趣的。特别是有一些我关注时间比较长的人,比如做音乐的人,我会想时代赋予他们身上的一些东西,我身上也有。有时是一些好的东西,有时是一些弱点,你看自己时未必可以看得那么清晰,但通过别人反观自己,会觉得一下理解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和外部世界的关系。”
在放慢的节奏里,理解自己和外界的关系
从写作时间来看,新书里只有《再见日食》完成于2019年。周嘉宁之后开始写《浪的景观》,没写多久,2020年就来了。
“疫情发生前的两三年,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整个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处于一个比较停滞的状态。我当时已经隐隐感觉到什么地方不太对,但直到疫情开始,它让我真正反观自身,发现原来生活和创作的很多地方都存在着停滞的问题。所以反倒是疫情这三年,当人在物理形态上真的被限制在某一个地方,我却重新获得了某种行动力,重新回到了和外界的互动,也更主动地去面对问题。”
她先让她的主人公动了起来,他们遍历上海、北京、南京、杭州、青岛……一直“在路上”。等他们上路了,她意外发现自己又找到了和社会、世界的沟通方式。“《基本美》是短篇小说集,里面的小说往往都做一个较为切片式的处理,但到了这本《浪的景观》,中篇的容量能够容纳我的主人公更多地行动起来,在虚构世界里去到其他地方,探讨一些别的问题。”
对她而言,书写2010年之后的事特别困难,她找不到一种特别准确而合适的语言,比如应该如何表述一个写公众号的职业。另外一点在于,她始终没有想清楚这十年的变化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又对他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十年的世界变化无比迅速,但所有的一切都还处于未知。她说过,她没有能力去写对自己来说还是完全未知的东西。
不难发现,近三年周嘉宁放慢了写作速度。去年年底整理书稿时,她几乎又把完成于2019年的《再见日食》重写了一遍。“我特别在乎准确的程度,每写完第一稿,我会一遍遍地修改每一个细节。”周嘉宁坦言道,一开始她对“慢”也有点焦虑,但现在她想用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去塑造一个世界,然后也以这种极其缓慢的速度陪伴她的主人公,在那个虚构的世界里成长。
在采访前一晚,她和朋友坐在延安绿地的草坪边上吃东西,看着天慢慢暗下来,然后竟有一群大雁飞了过去。这是周嘉宁第一次在上海看到大雁,它们还排成人字形,从北向南飞。当它们的身影掠过K11大楼,大楼的灯光从下往上打到了它们身上,它们看起来都是白色的,让周嘉宁感觉说不出的魔幻。
这样的时刻犹如她的每一个虚构时刻,现实退得远远的,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后记】
作为“90后”,我对新世纪初的印象其实很模糊,每每看到或者听说那时候的故事不免感叹“原来还能这样”,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亲近并喜欢这些故事。这本《浪的景观》的神奇在于,我有时会觉得它也是我这代人的故事,那里有热情,有迷茫,有一时冲动,有无疾而终,就好像是我自己对青年时代的念念不忘,在这本书里有了回响。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周嘉宁被认为不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作家,她更善于捕捉一种情绪、氛围,或者说人的内心。这种“善于”在新作里依然是成立的,有时合上书本,脑海中依然会有几个场景和人物的心绪挥之不去。但还有一个明显的感受是,从《密林中》到《基本美》再到《浪的景观》,周嘉宁越来越打开自己,去倾听外界的声音,寻找外界的痕迹,也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思考与回应。
“经过了一些时间转折点,我相信每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会有自己的变化,这些变化或许还不显现。但所有的变化到最后都会变成更大的力量,进而影响社会,影响世界,卷入充斥着作用和反作用力的更大的磁场中。”周嘉宁坦言,“做21世纪初的时间考古”并不是为了重建时代,而是想要为充满不确定的当下寻找一点线索,这些线索汇集到一起,或许可以指向一个更明确的所在。

 中国文艺网
中国文艺网 文艺云APP
文艺云APP